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9
波洛卓夫想把自己控股和亲自管理的那家硬脂工厂盘出去。经过半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的积极寻找,他终于遇到了买主。买主的名片上写的是“Charles Beaumont”,读起来不是“查理·波蒙”,像外行那样来读,而是应读成“查理士·毕蒙特”,当然应该这么读。买主是伦敦一家收购脂油和硬脂的霍奇逊—洛特公司的代理人。在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和艰难的行政管理状况下,合股公司已举步维艰。然而,在具有雄厚实力的大公司手中,却能带来巨大的利润。如果投入50—60万,就可指望得到10万卢布的利润。代理人办事很诚恳,他先认真地考察了工厂,认真地审查过工厂的账簿,之后才向公司提出报告建议盘下这个工厂。然后他同厂方就工厂出卖事宜进行谈判,谈判历时良久——这是我国一般股份企业的特性。连那些最有耐性、围攻特洛伊①城10年而毫不气馁的希腊人跟他们谈判恐怕也会觉得受不了的。在整个谈判阶段,波洛卓夫像对待要人一样,对这位代理人竭力奉承,并且常常邀请他到家进餐。代理人回避这些奉承,好长时间没有答应去家中吃饭。可是有一次他同工厂董事会的谈判搞得太久,又累又饿,终于答应到住在同一层楼的波洛卓夫家去吃午饭了。
10
查理士·毕蒙特也和每位查理士、约翰、詹姆士、威廉一样,他不大喜欢向外人披露心曲、侃谈隐私。但是,当别人问起的时候,他也会寡言少语,非常明了地说上一些自己的历史。他说他的家族源于加拿大,确实在加拿大居民中有几乎半数是法国移民的后裔,他的家族也是如此。因此,他的姓氏是法国式的,他的面貌与其说像英国人或美国人,莫如说更近于法国人。他又说,他的祖父从魁北克近处迁到了纽约,这也是常有的事。在迁居时他父亲还是个孩子,后来在此长大成人。这时我国一位从事农业的进步人士的富翁,突然想到要在克里米亚南岸搞棉花种植业来取代那里的葡萄园。他并且托人在北美找个管理人,结果就找到了生于加拿大而住在纽约的詹姆士·毕蒙特,他根本对棉花种植一无所知,正如我和读者诸位在彼得堡或者库尔斯克没有见过阿拉拉特山②一样,这在进步分子当中是常有的事。确实,事情搞糟并不是由于这位美国管理人对种棉业的无知,因为在克里米亚搞棉田就和在彼得堡种葡萄一样不可能。但是,即使这一点被证实之后,这位美国管理人仍然被解除了种棉工作,他到坦波夫省一家工厂当了酿酒师,他在那儿度过了余生,在那儿得了儿子,可是不久又死去了妻子。将近65岁高龄,他积攒了一些钱,忽然想回美国,并且真的回去了。那时查理士20左右岁。父亲去世之后,查理士很想返回俄国,因为他出生在坦波夫省乡下,又在那儿生活了将近20年,他感觉自己是个俄国人。他和父亲在纽约生活期间,他在一家商店的经理处当职员。父亲去世之后,他转到伦敦一家霍奇逊一洛特公司的纽约办事处供职,他知道该公司在彼得堡有业务,他就尽力表现,竭力想谋求一个在俄国的位置,他说他非常了解俄国,就像对自己的祖国一样熟悉。有这样一名职员驻在俄国对公司当然十分有用,于是他被调往伦敦经理部,考试合格,便于去波洛卓夫家吃午饭的半年以前,他赴彼得堡,给这家专做脂油和硬脂生意的公司作代理人,年薪500英镑。这位毕蒙特,由于出生于坦波夫省,又在那里生活了近20年,当时在周围20、50甚至100俄里之内,他所能看见的只有一个美国人或英国人,那就是他的父亲,而他父亲又整天呆在工厂里——毕蒙特的一切完全与这段历史实情相符。查理士·毕蒙特说一口纯正的俄语,跟地道的俄国人一样,他的英语说得虽然也流利、漂亮,但是毕竟不是那么字正腔圆,他是一个到了成年才在英语国家生活的人,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①特洛伊,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古代城市。关于特洛伊的传说是古希腊文学以来最著名的题材,荷马的《伊利亚特》《奥德赛》以及其他许多佚史著作中均有描述。据传说特洛亚帕里斯与斯巴达王墨涅拉奥斯的王后海伦私奔,引起这场长达10年的战争。②阿拉拉特山有两处,一处指在亚美尼亚的阿拉拉特山,一处在美国。——————
11
毕蒙特发现在一块吃午饭的只有三个人:除了自己以外,便是老人和一位非常可爱而又有几分心事的金发女郎,那是他的女儿。“我从来没有想到,”波洛卓夫吃饭时说,“这些工厂股票对我的重要性!老年人遭受这样一次打击是很难过的。好在卡佳倒不在乎我给她的财产带来的损失,就是我活着的时候,这宗财产也是与其说该属于我,倒不如说该属于我女儿。因为她母亲带来很多钱,我的钱不多。当然我把每个卢布增值成20个,所以,从另一方面说,这笔财产中我的血汗钱比继承到的更多。我真是付出了千辛万苦啊!那需要多大的本事啊,”老人用这种自负的口吻议论了许久,“我的财产是用血汗,更主要的是靠聪明才智挣来的。”他讲完这番话后,在结语中又把开头说过的话重复一遍,说遭受这样一个打击很难过,如果卡佳再感到痛苦,他恐怕早就疯了,可是卡佳不仅自己不怜惜,还给他老头子很多慰藉。或许由于美国人的习惯,看到人家骤然成巨富也罢,倾家荡产也罢,都视为平常,也或许是由于他个人的性格所致,毕蒙特既不愿赞美那挣来过三四百万巨资的大才大智,也不愿对这破产者表示痛心,何况破产以后还有余力雇用一个好厨子。但是他必须敷衍几句,表明他对于这篇冗长的演说中某些话的同情,因此他说:“是的,全家团结一致来承受不愉快的事情,那就轻松多了。”“您这话有点儿含糊,卡尔·雅科夫利奇。你以为卡佳有心事是因为她在惋惜那笔财产吗?不,卡尔·雅科夫利奇,不,您冤枉了她。我和她有另外一种痛苦,我们对人失去了信心。”波洛卓夫用半开玩笑半当真的口气说。像一个经验老道的长者谈论孩子的善良可是又十分幼稚的意见时那样。卡杰琳娜·瓦西里耶芙娜脸忽地红了。她不高兴父亲扯到她的感情上去。但是这不能怪父亲——除了父爱以外,还有另一个人所共知的原因。如果无话可谈而房里正好有一只猫或狗,人们就会谈猫论狗;如果连猫和狗都没有,就聊孩子;只有碰到第三种情况,即完全没有了聊天的资料,就只好说天气。“不,爸爸,您不用拿这么高雅的理由来解释我的心事。您知道,我只是生成一个不快活的性格,我就是爱忧郁。”“快活不快活每个人可以各随其便,”毕蒙特说,“可是苦闷,照我的看法,却是不能原谅的。在我们的兄弟英国人中间苦闷是普遍现象;我们美国人可不知道什么叫苦闷。我们没有时间苦闷:我们的事情太多了。我认为,我觉得(他改正了自己的美式英语的词句),俄国人民也应该看到自己正处在同样的情况中:我想他们手头也有许许多多事情要做。而我在俄国人身上看见的确实完全相反,他们很容易忧郁苦闷。在这方面,连英国人也远不能跟他们相比。全欧洲,包括全俄国在内,都骂英国社会是世界上最沉闷的社会,不过它比起俄国社会来还是要热闹、活跃、快乐得多,就像法国在这方面胜似英国一样。而你们的旅行家还对你们大谈英国社会的沉闷!我不懂这些人怎么不睁开眼睛看看自己家里的事!”“俄国人忧郁是有道理的,”卡杰琳娜·瓦西里耶芙娜说道,“他们有什么事好做呢?——他们无事可干,他们不得不垂手闲坐着。您给我指出一个事业,我也许就不会烦闷了。”“您想给自己找一个事业?啊,这恐怕还是可行的吧;您可以看出您周围的人是那么无知——请原谅我这样批评你们的国家,你们的祖国(他又改正了自己英国式的词句),然而我自己也是在这儿长大的,我把它当作自己的祖国,所以我才不客气,您可以看出这个国度有土耳其似的无知,日本似的衰弱。我要照你们的诗人的样子说一句:我恨你,正是因为我爱你,如同爱我自己的祖国。这儿确有许多事可做。”“不错,可是单独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女人,能做什么呢?”“但是你就做了,卡佳,”波洛卓夫说,“我对您泄露她的一个秘密吧,卡尔·雅科夫利奇。她为了解闷,正在给一群女孩子教书呢。她的学生天天来,她为她们从10点忙到1点,有时候还更长一些。”毕蒙特用尊敬的眼光望着卡杰琳娜·瓦西里耶芙娜:“这才像我们美国人啊——当然,我所指的美国人只是指北部各自由州的人;南部各州却比墨西哥更坏,差不多跟巴西一样讨厌(毕蒙特是激烈的废奴主义者)——这才像我们啊,既然如此,您为什么还苦闷呢?”“难道这算得一个重要的事业吗,毕蒙特先生?这不过是解解闷罢了,我是这样想的,也许我想错了,也许您会叫我唯物主义者……”“您还想听听来自把我们看作唯利是图,一切为金钱的民族的人的责备吗?”“您是在开玩笑,我可是当真害怕,怕对您说出我的意见——您可能认为它像蒙昧主义者怕鼓吹的教育无益论。”毕蒙特想道:“原来如此!难道她也了解这些?这倒很有意思。”“我自己就是蒙昧主义者,”他说,“我拥护南部各州的不识字的黑奴,却反对他们的主人——对不起,我的美国式的憎恨把话扯远了,但是我很想听听您的意见。”“我的意见很平常,毕蒙特先生,不过它倒是从生活中得来的。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太片面,而且,它所接触的那一面还不是希望为人民谋福利的人应该关心的最要紧的一面。我这么想:要使人们有饭吃,他们自己接着就能学会读书。应当从吃饭问题入手,不然我们将白费时间。”“您为什么又不像您应当做的那样,从这件事入手呢?”毕蒙特已经有点儿兴奋地说,“这是办得到的,我知道一些例子,在我们美国。”他补充说。“我刚才对您说过:我一个女子能做什么呢?我不知道从哪儿入手,就算知道,我哪有机会?女孩子在各方面都受着束缚。我只有在自己房间里才能独立自主。我在自己房间里做得出什么来呢?只好把书本摆在桌子上,教人家读读书。我一个人能上哪儿去?我一个人能够结识谁?我一个人能够做什么事呢?”“你把我说成是一个专制魔王了吧,卡佳?”做父亲的说,“自从你给了我那个教训以后,我在这方面可一直没有犯什么错。”“爸爸,我真是觉得脸红,当时我是小孩子啊。不,爸爸,您很好,您没有压迫我。压迫我的是社会。毕蒙特先生,听说美国的女孩不这样受束缚,这是真的吗?”“是的,这是我们可以自豪的地方。当然,就在我们那儿,离理想差得很远,但是比起你们欧洲人来到底好多了。人家对你们说我们的妇女多么自由,那倒是真的。”“爸爸,我们上美国去吧,等毕蒙特先生先盘下了你的工厂,”卡杰琳娜·瓦西里耶芙娜开玩笑说,“我要在那儿干点什么事情。啊,那该多高兴啊!”“在彼得堡也完全可以找到事干。”毕蒙特说道。“请说说看。”毕蒙特迟疑了两三秒钟。他心里想:“我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呢?通过谁去了解一下呢?”“您没有听说?——有人正在试验把最近经济学家研究出来的原则运用到实践中去:您知道这些原则吗?”“嗯,我读过,这大概是很有意思,很有益处的。我也能参加吗?哪儿可以找到呢?”“这是吉尔沙诺夫太太创办的。”“谁?她的丈夫是医生吧?”“您认识他?他没有对您说起这件事情?”“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他还没有结婚。我害了重病,他来过几次,救了我的命。啊,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太太可像他?”但是怎样才能跟吉尔沙诺娃认识呢?由毕蒙特把卡杰琳娜·瓦西里耶芙娜介绍给吉尔沙诺娃吗?——不行,吉尔沙诺夫夫妇连他的姓氏也没有听见过。其实无需什么介绍:吉尔沙诺娃估计也会欢迎这个同情者的。应该到吉尔沙诺夫供职的地方去打听他的住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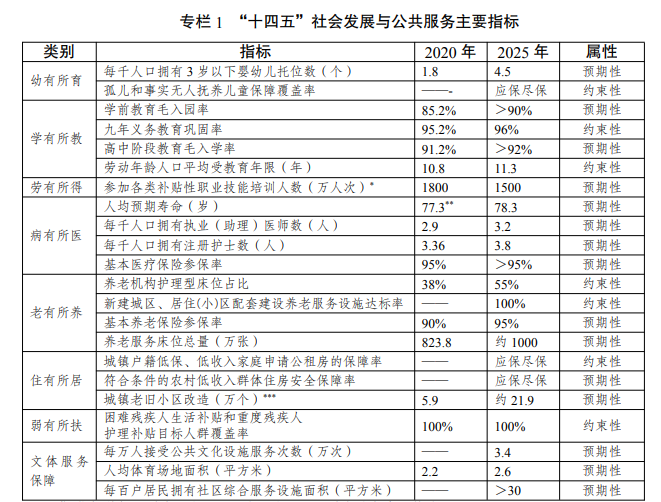


















![凌云县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III级/较重] 【2023-05-07】|全球热门](http://imgs.hnmdtv.com/2022/0610/20220610022641488.jpg)







